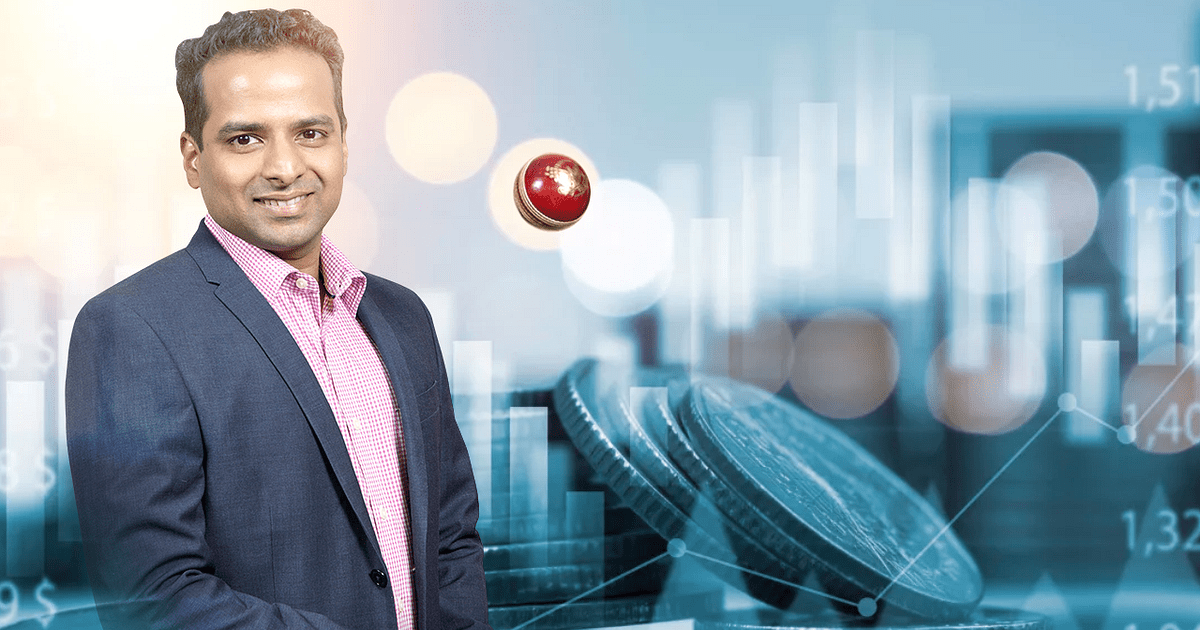AI 智能摘要
我偶然成為了一名投資者。 大學期間,我對股票市場沒有太大興趣。 體育頁面和 RK Laxman 的卡通是我關心的全部。 畢業後,我開始在 AF Ferguson & Co.(AFF,現在是 Deloitte Haskins & Sells 的一部分)實習,那時我開始了解企業。 即便如此,市場也不在我的關注範圍內。 我很想知道水泥是如何製造的以及抗壓強度意味著什麼,但對 ACC 的股價不感興趣。
當我在 2001 年原始技術狂熱的高峰期進行第一次投資時,一切都改變了。一天早上,一位同事衝進 AFF 辦公室,說「100% 小費」。 我什至沒有費心去問 100% 是表示這是肯定的還是預期回報的一種方式。 我也沒有問他為什麼一家熱門科技公司以北印度一個風景秀麗的蘋果種植州命名。

BSE 大樓和 2000 年代初期的孟買天際線。 (攝影師:Scott Eells/彭博新聞)
我個人承擔了這一損失,並決定從這個叫「先生」的騙子那裡追回我的一萬盧比。 市場’。 那是市場出現問題的時候,我被吸引住了。我繼續研究企業以及股票價格變化的原因,但在 2001 年崩潰後的幾年裡,我根本沒有投資。 我下一次買的股票是2004年的Shree Cement。實習期間,我花了很多時間審計水泥公司,對行業有了一定的了解。 理由很簡單。 Shree 是一家低成本製造商,在基礎設施帶動的需求增長可能很高的地區設有工廠。 它還在進行資產負債表修復,如果事情進展順利,將提高股東回報。 另外,這次的投資是基於自己的分析; 不涉及小費。 我不記得確切的購買價格,但它在每股 200 盧比附近,我買了 20 股。
不過我記得退出價格。 該股票表現非常好,2006 年中期的價格為 1,000 盧比。 我要結婚了,不得不賣掉 Shree 的股票來購買白色家電。
我從銷售中獲得的 20,000 盧比的大部分用於購買我們仍然擁有的洗衣機。 夫人有時會發現我盯著它看,因為以今天的 Shree Cement 價格計算,將近 60 萬盧比,我敢肯定它是該國最昂貴的洗衣機。
我作為個人投資者的旅程真正開始於 2011 年。我已經開始積累一些可投資的盈餘,那時我為個人投資制定了一些基本規則。
我作為個人投資者進行的第一筆嚴肅交易是在 2011 年 8 月購買了 Cholamandalam Investment and Finance (CIFC),我仍然持有該股票。 在我們進一步討論之前,有兩件事需要澄清。
首先,與 Twitter 上按市值計價的屏幕截圖不同,這不是一篇幸災樂禍的帖子。 截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BSE 500 中有 40 多家公司的十年複合年增長率優於 CIFC。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沒有吹牛的權利,但以 33% 的複合年增長率,沒有人可以說 CIFC 是一項糟糕的投資。
其次,我所有的個人投資都是在我前僱主的合規規則範圍內完成的。 事實上,10 只股票投資組合和永久持有期的規則來自這樣一個現實,即我沒有太多的帶寬進行個人交易。 在過去的十年中,平均而言,我每年進行的交易不到三筆。
我與 CIFC 的第一次會面發生在 2011 年 7 月。我在金奈與大公司會面了幾天,下午有一個小時的空閑時間。 我打算在 Dare House 與另一家 Murugappa 集團公司會面,我決定與 CIFC 會面,作為其辦公室的填充物。 前一天晚上我翻閱了年度報告,我所看到的並沒有讓投資組合經理對我感興趣。 市值為 1,800 千萬盧比,自由流通量略高於 20%。 即使我喜歡它,在機構投資組合中建立頭寸也將是一個挑戰。 是的,該公司在 2011 財年出現了一些好轉的跡象,但其賬麵價值在 2004 財年和 2011 財年之間保持不變。 股本回報率為個位數,股票的交易價格已經遠高於賬麵價值。 我關閉了年度報告,並在腦海中將其標記為「行業洞察」互動。
我記得第一次參加 CIFC 會議時的三件事。 一,首席執行官 S Vellayan 坐在開放式辦公室里,坐在瑞士舞會上,而不是椅子上。 聽得見的每個人都了解整個會議。 第二,Vellayan 坦率地談到了過去幾年的錯誤,尤其是不合時宜地涉足個人貸款;第三,我們在一張畫有三角形的幻燈片上花費了大部分會議時間。
Vellayan 的直率、思路清晰以及願意談論數字指標作為進度的晴雨表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等待另一個季度結果,只是想看看 CIFC 是否言出必行,他們做到了。 我寫了一個基本原理,基本上記錄了與 Vellayan 的「三角」討論,並於 2011 年 8 月中旬購買了價值 25 萬盧比的 1,650 股股票。此後,這些股票經歷了 5:1 的拆分,最初的 250 萬盧比的價值超過了盧比今天 460 萬; 不包括股息,複合年增長率超過 33%。
這十年發生了很多變化; 在經濟、金融服務領域以及 CIFC 本身。 我的投資方法是沃倫巴菲特所說的「接近懶惰的嗜睡」。 我曾經關注季度數字,偶爾通過電話和會議與 CIFC 代表互動。 只要發起人的意圖和能力以及增長機會保持不變,我就不會過多關注監管變化、首席執行官變動、季度失誤、每月股價波動,甚至估值。 沒有市凈率與股本回報率圖表,沒有自上而下的視圖,沒有相對回報比較。
但昏昏欲睡並不意味著我從擁有 CIFC 的十年中學到了什麼。
從第一次會議開始,Vellayan 就談到了總資產回報率 (RoTA) 的驅動因素。 隨著時間的推移,對 RoTA 變化的疊加增長和資本要求成為我分析貸款業務的首選框架。
大約十年前,他還談到了技術的使用,並在他的辦公室展示了一個用例。 2012 年,館藏工作人員手持手持設備上傳館藏詳細信息,而無需帶著一大堆紙回到辦公室。我們討論了如何將反周期構建到單線業務中; 通過選擇相關性很小或負相關的產品線。 最令人著迷的會面是 Vellayan 在卡車車廂里描述了他從德里到孟買的旅程。 我與業務主管和首席財務官 Arul Selvan 的會面也很有見地,重要的是,總體信息始終保持不變; 跨時間跨人員。
那麼這一切有什麼意義,你會問。 這個專欄是由與我 28 歲的保齡球教練的談話引發的,他告訴我執教是他的愛好,而「在 F&O 進行日間交易」是他的工作。
我告訴他要小心,他自豪地補充說,他不冒險,因為他從不收貨。 在 BTST(今天買入,明天賣出)、Telegram 聊天、實時「到期交易」會議和每日損益表的嘈雜聲中,我希望長期投資的微弱聲音出現在那裡。 即使沒有其他人這樣做,我希望至少我的保齡球教練會讀到這一點。
Swanand Kelkar 是摩根士丹利的投資者和前董事總經理。 觀點是個人的。
此處表達的觀點是作者的觀點,並不一定代表 BloombergQuint 或其編輯團隊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