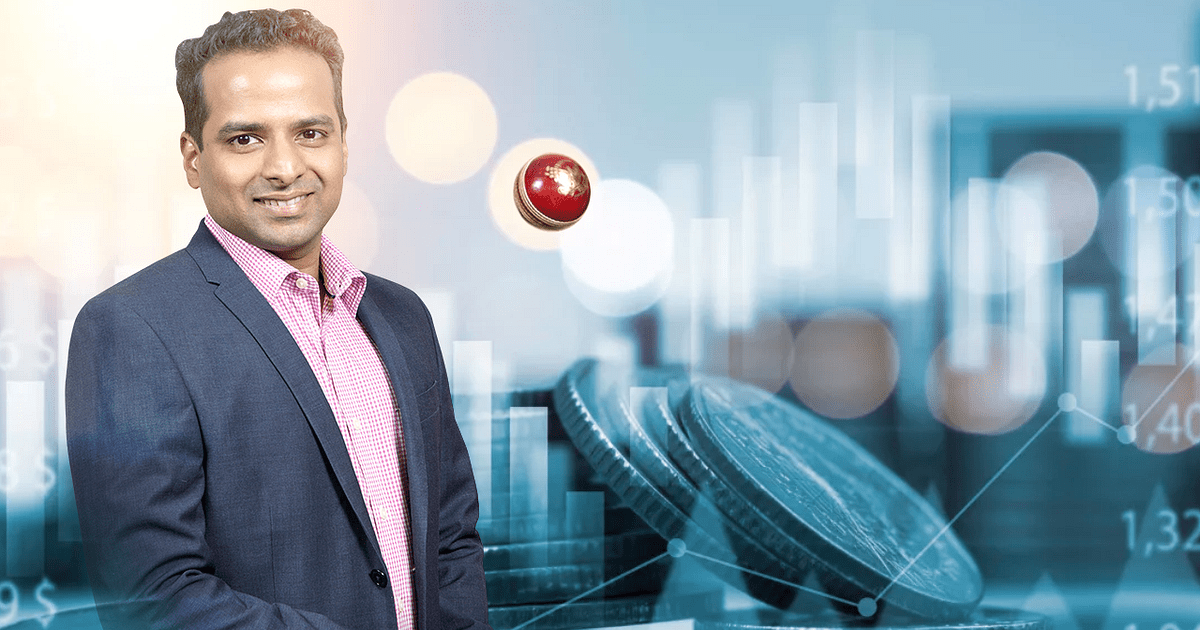AI 智能摘要
我偶然成为了一名投资者。 大学期间,我对股票市场没有太大兴趣。 体育页面和 RK Laxman 的卡通是我关心的全部。 毕业后,我开始在 AF Ferguson & Co.(AFF,现在是 Deloitte Haskins & Sells 的一部分)实习,那时我开始了解企业。 即便如此,市场也不在我的关注范围内。 我很想知道水泥是如何制造的以及抗压强度意味着什么,但对 ACC 的股价不感兴趣。
当我在 2001 年原始技术狂热的高峰期进行第一次投资时,一切都改变了。一天早上,一位同事冲进 AFF 办公室,说“100% 小费”。 我什至没有费心去问 100% 是表示这是肯定的还是预期回报的一种方式。 我也没有问他为什么一家热门科技公司以北印度一个风景秀丽的苹果种植州命名。

BSE 大楼和 2000 年代初期的孟买天际线。 (摄影师:Scott Eells/彭博新闻)
我个人承担了这一损失,并决定从这个叫“先生”的骗子那里追回我的一万卢比。 市场’。 那是市场出现问题的时候,我被吸引住了。我继续研究企业以及股票价格变化的原因,但在 2001 年崩溃后的几年里,我根本没有投资。 我下一次买的股票是2004年的Shree Cement。实习期间,我花了很多时间审计水泥公司,对行业有了一定的了解。 理由很简单。 Shree 是一家低成本制造商,在基础设施带动的需求增长可能很高的地区设有工厂。 它还在进行资产负债表修复,如果事情进展顺利,将提高股东回报。 另外,这次的投资是基于自己的分析; 不涉及小费。 我不记得确切的购买价格,但它在每股 200 卢比附近,我买了 20 股。
不过我记得退出价格。 该股票表现非常好,2006 年中期的价格为 1,000 卢比。 我要结婚了,不得不卖掉 Shree 的股票来购买白色家电。
我从销售中获得的 20,000 卢比的大部分用于购买我们仍然拥有的洗衣机。 夫人有时会发现我盯着它看,因为以今天的 Shree Cement 价格计算,将近 60 万卢比,我敢肯定它是该国最昂贵的洗衣机。
我作为个人投资者的旅程真正开始于 2011 年。我已经开始积累一些可投资的盈余,那时我为个人投资制定了一些基本规则。
我作为个人投资者进行的第一笔严肃交易是在 2011 年 8 月购买了 Cholamandalam Investment and Finance (CIFC),我仍然持有该股票。 在我们进一步讨论之前,有两件事需要澄清。
首先,与 Twitter 上按市值计价的屏幕截图不同,这不是一篇幸灾乐祸的帖子。 截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BSE 500 中有 40 多家公司的十年复合年增长率优于 CIFC。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没有吹牛的权利,但以 33% 的复合年增长率,没有人可以说 CIFC 是一项糟糕的投资。
其次,我所有的个人投资都是在我前雇主的合规规则范围内完成的。 事实上,10 只股票投资组合和永久持有期的规则来自这样一个现实,即我没有太多的带宽进行个人交易。 在过去的十年中,平均而言,我每年进行的交易不到三笔。
我与 CIFC 的第一次会面发生在 2011 年 7 月。我在金奈与大公司会面了几天,下午有一个小时的空闲时间。 我打算在 Dare House 与另一家 Murugappa 集团公司会面,我决定与 CIFC 会面,作为其办公室的填充物。 前一天晚上我翻阅了年度报告,我所看到的并没有让投资组合经理对我感兴趣。 市值为 1,800 千万卢比,自由流通量略高于 20%。 即使我喜欢它,在机构投资组合中建立头寸也将是一个挑战。 是的,该公司在 2011 财年出现了一些好转的迹象,但其账面价值在 2004 财年和 2011 财年之间保持不变。 股本回报率为个位数,股票的交易价格已经远高于账面价值。 我关闭了年度报告,并在脑海中将其标记为“行业洞察”互动。
我记得第一次参加 CIFC 会议时的三件事。 一,首席执行官 S Vellayan 坐在开放式办公室里,坐在瑞士舞会上,而不是椅子上。 听得见的每个人都了解整个会议。 第二,Vellayan 坦率地谈到了过去几年的错误,尤其是不合时宜地涉足个人贷款;第三,我们在一张画有三角形的幻灯片上花费了大部分会议时间。
Vellayan 的直率、思路清晰以及愿意谈论数字指标作为进度的晴雨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等待另一个季度结果,只是想看看 CIFC 是否言出必行,他们做到了。 我写了一个基本原理,基本上记录了与 Vellayan 的“三角”讨论,并于 2011 年 8 月中旬购买了价值 25 万卢比的 1,650 股股票。此后,这些股票经历了 5:1 的拆分,最初的 250 万卢比的价值超过了卢比今天 460 万; 不包括股息,复合年增长率超过 33%。
这十年发生了很多变化; 在经济、金融服务领域以及 CIFC 本身。 我的投资方法是沃伦巴菲特所说的“接近懒惰的嗜睡”。 我曾经关注季度数字,偶尔通过电话和会议与 CIFC 代表互动。 只要发起人的意图和能力以及增长机会保持不变,我就不会过多关注监管变化、首席执行官变动、季度失误、每月股价波动,甚至估值。 没有市净率与股本回报率图表,没有自上而下的视图,没有相对回报比较。
但昏昏欲睡并不意味着我从拥有 CIFC 的十年中学到了什么。
从第一次会议开始,Vellayan 就谈到了总资产回报率 (RoTA) 的驱动因素。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 RoTA 变化的叠加增长和资本要求成为我分析贷款业务的首选框架。
大约十年前,他还谈到了技术的使用,并在他的办公室展示了一个用例。 2012 年,馆藏工作人员手持手持设备上传馆藏详细信息,而无需带着一大堆纸回到办公室。我们讨论了如何将反周期构建到单线业务中; 通过选择相关性很小或负相关的产品线。 最令人着迷的会面是 Vellayan 在卡车车厢里描述了他从德里到孟买的旅程。 我与业务主管和首席财务官 Arul Selvan 的会面也很有见地,重要的是,总体信息始终保持不变; 跨时间跨人员。
那么这一切有什么意义,你会问。 这个专栏是由与我 28 岁的保龄球教练的谈话引发的,他告诉我执教是他的爱好,而“在 F&O 进行日间交易”是他的工作。
我告诉他要小心,他自豪地补充说,他不冒险,因为他从不收货。 在 BTST(今天买入,明天卖出)、Telegram 聊天、实时“到期交易”会议和每日损益表的嘈杂声中,我希望长期投资的微弱声音出现在那里。 即使没有其他人这样做,我希望至少我的保龄球教练会读到这一点。
Swanand Kelkar 是摩根士丹利的投资者和前董事总经理。 观点是个人的。
此处表达的观点是作者的观点,并不一定代表 BloombergQuint 或其编辑团队的观点。